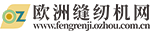君子玉言/三城誌\小 杳-天天短讯
北京沙尘暴的几天,住在办公室不敢出门,以免当“人肉吸尘器”,并加重感冒。毕竟口罩戴得再严,也挡不尽漫天沙尘。办公室窗户没开,窗台、桌上、地面还是浮了一层薄薄的沙,空气中弥漫着土的味道。这沙,是躲也躲不及的沙。
回到老家,窗外是江南滴也滴不完的雨。淅淅沥沥的清明雨,落在芭蕉叶上、落在天井里,落在母亲养的花上──吊兰、绣球、薄荷、杜鹃,都长得极好。
不自觉地想起香港,那里夜晚的窗外,是看也看不透的墨色大海。
 【资料图】
【资料图】
特别欣赏的作家葛亮对其故乡和客居的香港,有十分恰切的称呼──他称故乡南京为“家城”,称现在生活的香港为“我城”。他常常由对两座城市的观照,思考因循于不同环境、生长路径所塑造出的城市或个人的独特性。
每座城市都有自己渗在骨子里的“範儿”,这在千城一面的趋同大势中,成为了每座城市最后保留的自尊,不至于为他者完全重叠淹没。足迹亦心迹,经历不同城市的生活,每物每人都在这个过程中不知不觉形塑着属于自己的“範儿”。
对于我,故乡、北京、香港这三个地方,应该是:家城、我城、客城吧。我的想法与写作常常不自觉地在三城之间跳跃,那是思维这个家伙自己在跳来跳去,按都按不住。
对一个城市的感觉,与人的心境有关。
萧红来到香港时才三十岁,但已饱经忧患离乱。这个南国蕞尔之地给了她安静短暂的庇护,完成了《呼兰河传》这部传世之作。她创作的激情炽烈,身体却日渐衰弱。她在给友人的信中写到:“我来到了香港,身体不太好,不知为什么,写几天文章,就要病几天。大概是自己体内的精神不好,或者是外边的气候不对。”她一直在咳嗽、在沉思、在怀想、在写作……用燃烧生命的方式度过了在香江的最后岁月。
我曾在浅水湾影湾园酒店参加朋友的婚礼。酒店中西合璧,楼是新式的,中间洞空,像一个大大的回字;楼梯、廊柱、喷水池……却是老物件。过了马路拾级而下至沙滩,意外发现有一座雕塑和三组艺术长椅。雕塑为纪念萧红而建,由三十一只红色飞鸟组成,代表萧红短暂苦难的一生,每只鸟以不同姿势飞向不同方向,代表她跌宕飘零的经历。鸟的颜色由白渐变为红,是她生命色彩的写照。三组艺术长椅则为张爱玲而设计。子弹及茶几上的旧照片,代表战乱的时代背景和她的求学时期;椅上书籍和笔的雕塑,代表她的创作盛期;椅边的行李和扶手上的外套造型,代表在香港短暂的旅程。
张爱玲笔下的香港,是“酽酽的,滟滟的海涛”,还有“把窗帘都染蓝了”的那片海水。是“望过去最初触目的便是码头上围列着的巨型看板,红的,橘红的,粉红的,倒映在绿油油的海水里……”是这般浓烈的四季──春天,满山的杜鹃花在缠绵雨里红着,簌簌落落,落不完地落,红不断地红。夏天,夹道开着红而热的木槿花,像许多烧残的小太阳。秋天和冬天,空气脆而甜润,像夹心饼干。山风,海风,呜呜吹着棕绿的、苍银色的树。于张爱玲那样一个“刁钻”的人,“太喜欢这城市,兼有西湖山水的紧凑与青岛的整洁,而又是离本土最近的唐人街……”实属难得。
更喜欢葛亮文字里的香港,他既能敏锐地观察到物欲匆忙的所谓“中环价值”,也曾站在港岛电车末站的西环,体会这座城市的静谧和老旧。他在大学里静静地感受浓厚的人文气息和历史感,感受许地山、陈寅恪、朱光潜他们留下的痕迹。他笔下的香港古雅樸旧,也市井混杂,充满时光的交错感。不徐不疾,如他一向的儒雅舒缓。
“当你在这座城市生活久了,它的某些特性会深入到你的血液跟肌理当中,会很自然地影响你的思维模式,成为你表达方式的一部分。这不是你可以选择的,一旦你对这座城市的表达进入到这个场域,这个城市会选择你。”
家城是自身的来处,滋养了人的脾性、质底;我城是事业的栖息地,决定了人的站位;客城──幸好是香港──拓展了人的视野,让人更包容。故乡让人亲近松弛,京城的磅礴厚重让人敬畏,香港的多姿多元让人葆有新鲜感探究欲。三个城没有彼此排斥,没有彼此鄙薄,没有彼此羨慕。她们各自有各自的好与不够好,让我更加丰富平和,她们塑造了开阔的我。
在故乡,陪陪母亲、吃一餐带竹笋的土菜就好了;在京城,没有什么事不可被长安街的骑行治癒;在香港,坐一趟天星小轮吹吹海风、坐在西环的海边看一场壮丽的落日,就好了。
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