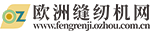视讯!《阿尔庇斯》第二章第三节
当时从冬眠中心接我时,藤野坐的是一辆全自动驾驶的汽车,全AI控制,只需扫描确认使用者信息后就能上车自动行驶。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公司租的车,租金不便宜。其实冬眠后的我是有权力拒绝丹生娱乐的合同的,他们没有把那份法律条文给我看,那台车也是为了充门面让我愿意签署合同的道具。现在藤野开的则是自己的车,很旧,与十年前,甚至半个世纪前的车并无太大区别。
 (资料图)
(资料图)
他在车上给了我响公司的那份合同,报酬对我来说很丰厚,衣食住行全包。但也很危险,需要前往战争的最前线。在那里,棘人造物源源不断地爬上岸。
“会有一个小队护送你,你只需要唱唱歌就行。”藤野如此说道。
我想起了奥利维亚的话,她就像是预知了一切,所以我学着她的模样呛回道:“说得真好听,这很危险吧?”
藤野大约是没想到我会这么跟他说话,沉默片刻回答了一个“是”字。
我看着他的侧脸,他抿着嘴,好像有什么难言之隐,我突然意识到他似乎也不想让我去。果然,他开口说道:“这是我们私下说的话,别让别人知道。据我了解,你不是第一批被选上的音乐工作者,先头那批觉得报酬太少或者太过危险都拒绝了合同,他们找你是因为刚刚苏醒的你应该急需用钱,以及……我们公司现在的情况。你明白了吗?”
融资的关键阶段,丹生娱乐不敢拒绝,所以公司会不断向我施加压力逼迫我同意这份合同,我从藤野的表情上理解了一切。
“看看这个吧。”藤野投影出了一篇新闻稿,日期是2042年10月14日,正好六个月前:
不飞鸟集团旗下的深海猎人蛟龙小队以全体阵亡的代价击退了棘人在东海的入侵,来自世界各地的群众自发纪念这二十七位英雄。不飞鸟集团CEO熊瑶飞女士表示:这些英雄们的牺牲是值得的,他们用生命证明了不飞鸟军工正走在有效打击棘人的正确道路上,这是为全人类作出的重大贡献。集团计划将会在太空建立一座纪念碑,纪念永垂不朽的英雄们。据悉,待该计划实施之后,人们可以通过不飞鸟太空研发的观星APP找到纪念碑的位置以瞻仰纪念。如果要一睹纪念碑的风采,则可以搭乘不飞鸟太空电梯前往近地轨道搭乘直达的太空车……
“那是不飞鸟的特种部队,世界首支专门对抗棘人的部队。但那些专家们全都牺牲了……陈,你的邻居说的没错:选择权在你手上。”
我没有回答他,他也不期望我的答案。他载着我回到公司,在办公室门口,我看见正在训斥久美小姐和杰弗瑞先生的社长,在我身旁的藤野先生也停下了脚步,眼神少见的慌乱。
他最终看向了我,同他一起的,还有所有留在这里的丹生娱乐员工。我还能看到他们的眼神中藏着妻子丈夫,老人与孩子。
我闭上眼,他们仍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阻止着我回想奥利维亚的话语。
我明白了自己内心的答案。
一周后,我在距离阿德莱德的沙滩三百米处写下了人生第一段歌词:
云吞噬了太阳
战士占领了海岸
漂浮在卡布奇诺上的泡沫
抚平了温润的唇瓣
丹生娱乐和隔壁的安保公司关系不错,他们免费培训了我,我也得以顺利通过体能测试。其实有一个项目我拿了0分:射击。安保公司的师傅们跟我说:“不要想战斗,能跑才是最重要的。”
通过的消息传来后,我正式成了闲人,排练不需要去了,那支乐队的成员们都找到了下家,那将会是解散演唱会,不再需要我出场。我在办公室里无所事事,其他人也都对我很礼貌,甚至有些过度热情。只有久美小姐和杰弗瑞先生待我依旧,他们让我帮忙处理些杂物,临下班时问我:“下班后有空吗,出去逛逛?”
我就是在他们带我来的餐厅写下的这段歌词。
城市的海岸线在西边,这也意味着幸运的阿德莱德人能够看见海上落日。这家是离海岸线最近的餐厅,设在某个商场的三楼。靠窗的位置能看到在沙滩上训练的士兵们,除了他们,已经没人能够踏上这座城市的沙滩。
日头已经很低了,不出半小时就会沉入大海。就如我们三人的话,渐渐变少了。
“悦音。”最终开口的是久美小姐。我意识到她要说什么,将目光从熨着金边的云彩上挪开,只看了她一眼,便盯上了她身后正在自拍的情侣。
“所谓大人,就该保护孩子……我们是不是正走在一条罪恶的道路上?”
她不是在跟我说,而是跟她自己。
沉默回荡了半晌,那对情侣中的女生想让男生看看照片,却发现对方正沉迷于虚拟世界中,于是生气了。
“我来说吧。”打破沉寂的是杰弗瑞先生:“我有个计划,让你不用去悉尼,公司也不会完蛋。”
杰弗瑞先生的眼神坚定。他说了“我”,意思是他将会把所有责任往自己身上揽。松田久美显得很吃惊。
我不再去看那对情侣的吵嘴,而是望向沙滩。有不少穿深绿色作训服的士兵正在灰色作训服的指挥下训练,他们是陆军,前来支援海岸线。
“那代价呢?”我不再保持沉默,但他们沉默。
“我不想拖累你们。”我说:“藤野先生已经告诉我了。”
他们的计划的确会救下困境中的公司和我,但会导致他们妻离子散。
我眯起了眼,太阳从云层后钻了出来,夕阳打在我脸上,也照亮了他们的侧脸。
“等我回来,接着做我的部长吧。”
公良昕雨的手把着方向盘,目光在咖啡店和西装男身上来回转,咖啡店里盯梢的人已经起身,路边的汽车也隐隐有了动静,那些一定都是警察。
云层渐渐遮住了太阳,车里暗了下来,她深吸了一口气,想要抑制指尖的颤抖。
没事的。
她在心里对自己说。
她忽然坚定了眼神,右脚踩下油门,方向朝着西装男打去。
引擎的轰鸣点燃了后座另外两人,苏联人大骂一句,日本人则惊呼:“你疯了!”
公良昕雨咽了口水,喉间一滑,大声喊道:“我们只有这一次机会!”
“你会害死我们!”苏联人大骂着,却已经打开了手边的门,跳下车将受了惊吓的西装男拎起丢上了后座。
“啪”的关门声带着汽车晃了晃,公良昕雨瞪着面前的路,一脚油门逼散了已经亮出武器的便衣警察们。
“你个混蛋,那些是条子!”日本人冲公良昕雨大喊着。他帮苏联人拉扯着西装男,露出后背巨大纹身的一角。他曾是日本黑帮成员。
“他们不敢怎么样。”公良昕雨嘴硬道。但这是抓了个现形,不论警察是什么部门的都不会放过他们,后座的日本人也明白这个道理,他破口大骂,却碍于手下西装男挣扎的动作吐不出完整的句子。他最终给了西装男一拳,苏联人趁机控制住了他的双手,西装男终于消停下来。
就在此时,车外传来警铃声。公良昕雨看了眼后视镜,便衣车已经亮起红灯。
事已至此,后座的两人只能按计划进行。日本人掐着西装男的脖子问:“加藤凉介在哪儿?!”
西装男在惊恐的眼神下吐出断断续续的话:“加藤部长的行踪我怎么能知道?”
“你是他办公室的副主任,你会不知道?”
“真不知道啊!”
日本人的拳头又落了下来,他深知打人的方式,不会真正取了对方性命,这自然也是从黑帮学的。
与之相对的是苏联人,他在开始时骂了几句,现在反倒很安静,他一直瞥着驾驶座的公良昕雨,不知在想什么。
公良昕雨自然也从后视镜观察到了这一点,她很紧张,脚下的油门不自觉踩得更深,这会儿沉下声音开口:“连接他的端口。”
苏联人看了她一眼,最终丢下一句“待会儿再找你算账”便拉出了连接线。
公良昕雨的鬓间渗出了汗,抬手关闭了空调,苏联人又说:“有了,在札幌。一个小时后到东京。”
公良昕雨微微松了口气。
日本人抬手打晕了西装男,苏联人打开了门,将他丢出了车外。日本人打开通讯说:“一小时后,羽田机场。”
苏联人向车外啐了口唾沫,对公良昕雨说:“停车,我们去自首。”
公良昕雨看了眼后视镜,她没有再说话,缓缓踩下刹车。后座的苏联人却紧皱眉头:“不对劲,警察不见了。”
“去救人了?”
“不应该,他们有两台车。”
苏联人望向前座,忽然吃了一惊,他以为公良昕雨凭空消失了。直到他探身向前,才发现她正抱着头趴在方向盘上。他正觉得奇怪,突然听见外面传来车辆的轰鸣声,还未来得及反应,剧烈的撞击使他失去了意识。
等苏联人醒来时眼前只剩下雪花。他意识到是自己的视觉系统出了问题,身上也被什么东西压住,下半身失去了知觉。
他试图抬起身上的东西,可惜它纹丝不动。他放弃了,手垂下来时摸到了不少温热粘稠的液体,他一愣,旋即意识到那是血。
“……有人吗?”
他觉得嗓子火辣辣的疼,发出的声音也很奇怪。好在他还能听到声音,除了远处汽车驶过路面的震动,他还听见了脚步声,靴子踩在玻璃碎片上发出吱拉声,来人还踢开了一块类似钢板的东西。
“……松本?”
来人站定,没有回答,他只听见了小型机械的声音。
他的大脑一片空白,他知道接下来会是怎样的声音,他太熟悉了。
随着“砰”的一声,他死去了。
公良昕雨看见男人手中枪口冒出的烟很快被寒风吹散,不禁庆幸自己并不在汽车残骸之下。那人将枪收好,抬眼望了过来。
“辛苦了,公良小姐。加藤先生已经到东京了,感谢您的情报。”他用的是敬语。
“……二位才是辛苦了。”她又将目光投向男人身后的车,副驾驶坐着刚才被丢出去的西装男。
“走吧。”
公良昕雨看了眼男人的右手,这才点点头动了起来,走过男人面前时却屏住了呼吸。
预想中的拳头落下。
“加藤先生还让我转告您,他这辈子最恨叛徒。”
公良昕雨抬手捂着脸,沉默地坐上了那台车。
陈悦音与圆明拾级而上,走在峨眉山的林间。冬季的山中多了不少秃枝,能窥得更远。
“要是在夏秋季节,爬山客们看不见尽头,总觉得自己快到了。”
天很低,就像是给大地盖了一层白色的棉被,陈悦音看见山路向着云层中延伸,不由地微笑:“夏天我曾爬过一次,的确难受一些。”
台阶结了冰,两人不得不放缓了步子,任由冬风吹拂。他们已经爬了四个小时,路程却还未过半。
“上面有一间寺庙,进去歇一会儿吧。”
陈悦音点点头,抬头望去,云层比刚才更厚了。
“看来山上下雪了。”
她说得不错,两人赶到寺庙时天上就飘飘荡荡落下轻盈的雪花。陈悦音捧着热茶,坐在庭院里看雪落入绿色的池中,落在枝桠的上头,慢慢积起薄薄一层。忽然水花一溅,一条红尾自水中闪现,惊化了池里的雪,惊落了树上的白。
她很快就觉得有些冷了,不得不起身钻进寺庙的食堂。
食堂的师傅是俗家,圆明向他打了声招呼,他便下了两碗面。陈悦音还瞧见一旁的碗中铺底的红油以及备好的葱末。
她没有说什么,又续了杯热茶抬眼打量起食堂。食堂都是木桌椅,看着有些年头了,就连手上的茶杯也都是上世纪流行的搪瓷杯。饭点刚过,一位年轻和尚正在打扫卫生。冬季极少有香客前来,他也轻松许多,很快就收拾好了。
圆明看似认识那位小师父,与他微笑交流着最近玩的游戏,听起来两人都喜欢玩不再流行的单机游戏。两位同好的寺庙相距六百米,一个在山上,一个在山下,又是整座山最难爬的路段,一般人爬起来很吃力,但他们却经常这样跑上跑下地交流,也算是一种奇缘。
他们的交流很平和,但能听出他们对游戏的热爱。煮面的师傅吆喝了一声,陈悦音谢过师傅,取了木筷子和钢碗装的素担担面。上面摆着一些香菇、芽菜和花生碎。拌开面来,白色的碱水面便染上了些许红油美味的颜色。陈悦音吃了一口,的确是正宗四川担担面的味道。
圆明吃面很快,没一分钟便收拾了碗筷递进厨房。同好们又继续了话题,陈悦音就着谈话声望着这座千年古刹嘎吱作响的木窗,也不知这些木板与佛像见识了多少这样的落雪,多少这样的人。
曲终将尽,她谢过这边的菩萨,与圆明再次踏上旅程。